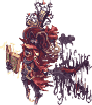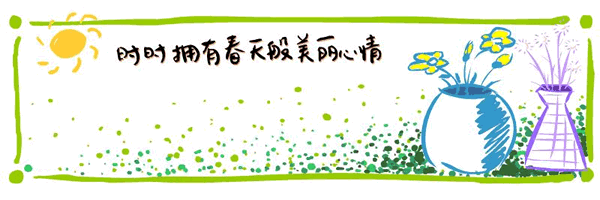|
    
 
 我们约会吧! 我们约会吧!
|
8#
 发表于 2006-4-8 22:42
发表于 2006-4-8 22:42
| 只看该作者
八
洪情,染疾,饥荒,几乎所有的灾害都在同时席卷了这个本安宁的乡镇。荒尸遍野,孤坟油生。人们开始恐慌,他们试图企求能被给予新生。于是,于是,女孩被送上了极刑台筑。她很安静,安静得让人错以为是个天使。人们站在台筑下,仰视,满目麻木及迫切。他们相信,只有女孩的死亡,才能换回天神的救赎。他们只要生存,而已。女孩看着脚下的潺潺人群,笑了。欠身,半躬。女孩感谢他们让她生活了十七年,尽管他们除了鄙夷,没有给予过什么。亟年站在祭台上,柔声叫着,阿悦。他,无力乏天。于是,只有等待,等待这个他算了半辈子的占卜。沉重的黑锁直直的穿过,女孩的锁骨, 铮铮地定在黑色玄铁的柱子上。血激化成墨黑色,沾染着女孩的白纱裙子。一大片一大片的疼痛,一大片一大片的流失,她似乎看到自己的身体渐渐的透明,然后支离破碎。女孩想,这是要死了吗,为什么这样地疼痛。手心的褐痣,似乎一张一合的在告别。女孩突然,怀念,怀念起,她的天使。哦,不。是恶魔。琰若。女孩低吟。
当这片墨黑的翅膀,抚过天际,所有人开始惧怕,黑色,恶魔,罪恶之源。他们叫嚣着,摄魂怪。纷纷逃离。男孩想,我又吓着他们了。既而摇了摇头。定定地停在女孩面前,眼神中,尽是怜悯。男孩说,这就是你的诅咒吗。女孩低头,说,是的,它足以让你重新出现,我的琰若。男孩用翅膀抚去女孩隐匿的泪水,缓缓地道,是的,你赢了。我回来了,你的琰若。女孩抬头,咯咯地笑着,原来,原来,她的琰若从未改变。手心的小痣勾起漆黑的羽毛,欢愉地笑着。她胜利了,用一生的占卜,换回了她的信仰。手指停留在小摄魂怪的墨黑翅膀上,很温暖。似要融化了般。
上帝说,要结束了。这个故事。转身看了看,自己的影子,说,为什么他们相信撒旦,而不相信上帝。影子狡黠地笑着,说,因为他们有罪恶。上帝叹了口气,道,孰不识上帝和撒旦只不过是一人的实虚。
九
女孩依偎在男孩的怀中,眼前是大片大片的血红和明媚,她转而一笑,嗫声道,琰若。琰若。琰。若。我的恶魔。她在等待,死亡及告别。炭黑的翅膀布满温暖。不是来世才有温暖,不是花容才有慕者,不是独孤才有清冽。于繁嚣华羽中,长大,消亡。翅膀合起,带着某些潮湿的液体,一并感念。女孩问男孩,琰若,如果我死了,是不是也会化为泡沫纷飞,随风祈祷。声音疲惫却欢愉。男孩思豫片时,道。会的。象珍珠般夺目,眩悦。女孩咯咯地笑了。笑男孩的一本正经,笑男孩恶俗蹩脚的比喻,笑这些蔽露在隐晦下的明媚华丽。这场劫数中,他们试图互相救赎,然,最后双双陷入,不厥的死潭。他们幸运地拥有,于是必须放弃。得到了,是为了失去时知道还有什么去怀念。女孩说,她累了,要睡了。躺在温存的翅膀上,嗅着淡漠的柠檬香味,象个婴孩般睡去,安详的,平和的。左手心的小痣开始安定。不再激越和狂妄。它安静地附在女孩的手心,听着血液慢慢停息流动。男孩从翅膀上拔下一羽墨色,放在女孩的手心中,褐色的小痣欢悦地笑着。它得到了属于它的依靠,于是他们互相告别。在这个无序的故事中,愿望及祈求逐然消亡。男孩抱起女孩,展翅的瞬息,林鸟哗然。象个天使般,游离傲天。羽毛从女孩的手心飘落,带着信仰。如果这便是结果,那么她爱上了。没有天悯哀歌,没有肃穆悼怀。我们的女孩,就这样,死了。恶魔,诅咒,不详。他们组成了场游戏,除了唾弃,得到相赖。男孩抱着女孩直冲天际,黑漆的羽翼,在日浴下咄咄刺眼。褐痣慢慢退却。
十
我知道,我是恶魔,令人厌恶的恶魔。这是我的事实,也是你的。请你陪我一起接受。
小摄魂怪把悦然轻轻地抱起来,纯白的棉裙缓然地划过小摄魂怪的手心,它们仍然温暖着,即使已然死去。午后,阳光灼热。小摄魂怪吻了吻女孩的眉心。身体已经开始僵硬和冷却。这是场即将开始的祭祀,华丽而绚目。小摄魂怪将女孩平放在木桥上,指尖划过女孩光洁的皮肤,一条血印。血从伤口汩汩涌出,它们似乎知道这是最后一个逃离的机会,而纷然涌动。血在指间印染,化却。小摄魂怪吮吸着手指上的液体,这是他第一次触及血。他一直相信,这是种混迹着最纯净和最肮脏的液体,既可玷污,亦可净化。他似有些疯狂的吞食着伤口上流出的液体,他们属于一个女孩,一个他可以花费所有精力去爱的女孩。所以他要全然拥有,这是属于他的。他强忍着恶心及眼泪,慢慢地撕下血肉模糊的锁骨,放在嘴中咀嚼,骨头和人肉在齿间撞击,强硬地吞并。这场激烈的摩擦,如同战争。兼并,而潦倒。最后一根骨头了,锁骨。女孩最喜欢的部位,亦是小摄魂怪喜欢的,晶透。小摄魂怪有些爱惜的将其放在手心擦拭,慢慢,慢慢的,如同最后的告别。夕阳下,一切安详而平宁,这是个普通的黄昏,没有飞鸟,没有微风,一切停息。小摄魂怪躺在木桥上,他太累了,抑郁了过久,承受了过久,需要休息,很长很长的休息。手中的锁骨,把玩着。它,犀利而尖锐。突然转手,直直刺向咽喉,如此猛烈,血溅在碳黑的翅膀上,如白雪般,清晰而光亮。翅膀终于干净了,终于,终于。小摄魂怪暗暗叹了口气,要走了,带着所爱的,一起走了。夕日,刺眼而晕旋。无论天堂还是地狱,结局都是一样的。选择了,放弃了,都是他的。好了,好了。再见了,他和他爱的在告别,眷恋是属于自己的,怀念是属于别人的。
血流淌着,顺着咽喉,顺着手指,他们是最终唯一得到幸福和自由的,他们叫嚣而欢呼。血被溪水包围着,欢叫着。于夕日落寞中,化为一流瑰红的画卷。
我们始终是孤独的人,即使有了依靠。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