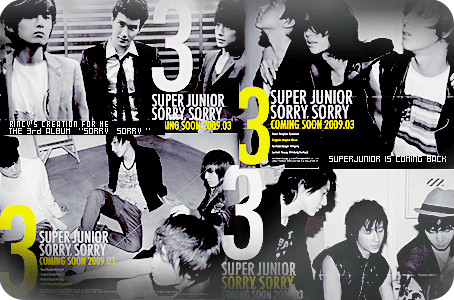|
   
- 帖子
- 1152
- 积分
- 1152
- 经验
- 1152 点
- 威望
- 69 点
- 金钱
- 5372 NG
- 魅力
- 1718
- 性别
- 女
- 来自
- NZ.AKL.苏州
- 注册时间
- 2002-12-12
 我们约会吧! 我们约会吧!
|
152#
 发表于 2006-6-27 14:21
发表于 2006-6-27 14:21
| 只看该作者
| 69. 无病呻吟
天蒙蒙亮的时候,我醒了。
我感觉自己仍然活着,有呼吸,有心跳。我手腕上的血口子已经凝固了,可能是我力气不够大,所以只割破了表皮,所以死不了。死的恐惧爬满了我的脸,突然我感到自己害怕死,也害怕为吴慰死,死的勇气常常只在刹那间,现在我后怕了,我抱着冰凉的被子,不停的发抖。
楼下的房东太太已经在开始做面包了,她每天6点起床,面包要经过搓条、下剂、成形,最后烘烤而成,自然比较费时,我披着上衣服,走到一楼,依在她的厨房门口,看她忙活着。
她看我来,说了声早,我说要一杯咖啡,她说小孩子最好喝牛奶,没给我,我说我已经二十多岁了,她却说她已经六十多了,所以我还是孩子,她硕大的身子在狭长的厨房里来来回回,显得很忙碌。
这时候门铃响了,我前去开门,来者是小P。
“怎么早?找我?”我有气无力地说。
“你没事吧?”他急切地问,我慌忙把贴了着胶布的手缩到袖子里。
“我会有什么事?”我反问道。
“那就好,我昨晚怎么也睡不着,想到那句你死我活再想你那个表情,突然觉得你会,你会死似的。”他搔搔头。
“你头发已经够乱了,别搔了!”我说,他显然还没有梳洗过,急切地赶来,头发乱如雀巢。
“那我回去了!”他转身要走。
“小P!”我拉住他,想了想说:“你相信预感这回事吗?”我把我的那只贴着胶布的手举起来呈到他面前。
“老天!你还真!这么说我的预感是对的!老天!”他把我的手托起来,仔细查看,又说:“快忘了那套东西吧,碟仙是迷信,是不科学的,它迷惑你了。”
“可是盘子真的动了啊!”我半信半疑。
“我想了一夜,我明白了。盘子为什么会动!那时候环境诡异,我们因为害怕发抖,所以搭在盘子上的手指也在抖动,所以微乎其微,但五个人相加,效果就出来,Ellen说说人越多越灵,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”他继续向我进言,希望我走出迷堆。
“小P谢谢你!”我真诚地说,我谢的不是他的劝解,而是他的探望。
“你想明白了吗?别做傻事了!好吗?”
“恩。”我木呆呆地点点头。
天越来越冷了,阁楼上是没有暖气的,房东太太叫我搬到Kim腾出来房间,我不同意,于是小P给我送了一床被子。
这段日子我开始寄情于写作,把被窝支成一个小帐篷,窝在里面,一页一页地写过去,写我父亲,写吴慰,偶尔也写Steven,蓦然,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。
自己创造这些字句,再用这些字句自残,这就是无病呻吟,小P说。他反对我的行为,他说我应该多出去走走。
我接到Steven的电话,他说要过了年要去美国读书了,说想在那之前来看看我。
他的新款的奔驰跑车停在我们学校门口,引路过的学生纷纷伫立观看。
“恭喜你!”我伸出手。
“谢谢!”他握着我的手不愿松开。
“别这样!”我轻轻地说,他把手松开,我赶紧缩了回来。
“我想请你吃饭,可以吗?”他说,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,我们从来没在外头下过馆子。
“恩。”我点头,算是了了他的心愿。
他带我到DE KOPEREN HOOGTE,我们走进大厅,当我看到巨型渔缸里的鲨鱼,便想起第一次和吴慰来这儿的情景。
“这鲨鱼好像越来越迟钝了。”我看着鲨鱼停在那里,一动也不动,再凶猛的动物长时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呆着难免成了二楞子,我想起小P这么描述我:再活泼的人在一个人老在房间里呆着也难免精神分裂。
人和动物其实都会被孤独打倒。
“你来过?”Steven惊奇地看着我。
“来过,很久很久以前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“那我们上去吧!”他拉着我进电梯。
Steven先我一步抱怨了:“这里上菜还真慢!以前我们打工的地方,快多了!”想必他是第一次来。
“这是温柔速度。”我想起吴慰的话,心一下沉,女人总是喜欢掏一句傻话来害自己难过,我又开始无病呻吟了,我抿抿嘴唇,想打消这个念头。
“听说Jacky回来了。”他说。
“回来了?”我几乎叫了出来。
“我上次看到你和他一起骑车去学校。”他解释道,原来是早些日子。
“你监视我们啊?”我故作轻松,送了一块肉进嘴里。
“不是!就是想远远的看看你,看看你们,看看你们的生活。”他凝视我。
“说真的你不戴眼镜帅多了。”我们彼此打量。
“但还是不如Jacky帅,对吗?”他又说。
“你请我吃饭,你老提他干什么?”他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虽然我知道他向来不识趣。
他低下头,不再说话。
吃完饭,他送我回家的路上,我思忖再三,还是把实情相告:“Steven,你能叫你爸帮我打听一下Jacky的事吗?他可能出事了。”
“是吗?那么你怎么办?”听罢,他错将我当成了受苦的主体。
“我没事!你能帮我找他吗?”
“好!我答应你。”Steven拿起我的手,又说:“我一定会让他回来的。
我……”
“什么?”我望着他,把手抽了回来。
“让我再吻你一次,可以吗?”他的眼底藏着丝丝的哀伤。
我合上双眼,感觉他冰凉的唇附了上来,他的泪水垂了下来,一直流到我唇边,让我尝到了自己对他的辜负。我在心里说:“Steven,如果有下辈子,我会好好爱你!”
70. 咖啡伴侣
临近圣诞节,房东太太要求我们全体房间大清洗,除了我自己的房间外,我的包干区还有二楼的浴室。我们房间的墙纸已经有些发黄了,吴慰曾经说过要在过圣诞节之前换了它,我看着直角墙上贴满了我们以前写得字条。
“生活就像一锅炒蛋饭,有时候蛋炒饭,有时候饭炒蛋。”这条是我写的,这让我想起我的“everything炒蛋。”
“生活就像剥洋葱,总有一页让你流泪。”这条是吴慰写的,那是我们在回忆以前打工的日子。
“此心忧太苦,把酒且狂歌,狂歌犹不足,呜呼我奈何?”这是吴慰写的小诗。
“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,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?”这一条是我和David因为谁洗厨房的锅子而发生争执时候,吴慰给我写的劝戒。
这面墙贴满了字条,贴满了回忆。
衣橱里的顶上有只红色的密码箱,沾满了灰尘,我拿抹布把它擦了一遍,觉得并不干净,于是干脆把它拿了下来,它并不太沉。
里面是什么?我幻想着。密码号有三个,会是什么呢?我寻思着。
“520!”我脑里闪过这几个数字。
我把密码拨好,果然能打开。有时候破解恋人的内心除了靠直觉,别无他法。
我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倒在塌塌米上。最上面是一本照相本,是他的家庭影集,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母亲,他的母亲皮肤如雪,很美,美得有些柔弱,看着看着,我发现她长得很像Suki,怪不得吴慰对Suki的事如此上心,愿意为她犯险,那是亲情在作祟。
红色锦盒里立着一枚戒指,我认的,它是他送给我,而我又还给他的那只。这戒指吴慰一直留着,但他后来又觉得当时买戒指的钱不干净,于是盘算着用工作后的第一份工资给我再买一只。
米色的长盒子里装着一些票据之类:2003年八月我们第一次去江心屿的船票、麦当劳的盒子、有天上人间KTV的帐单、还有登机牌……这些都和我有关,他曾经对我说过要把这些爱的证据留给我们的儿子,向他传授自己当年的求爱秘籍。我说万一生的女儿呢,他就说那就告诉她使这些招式的男人都是好男人。
长盒子里还有一个盒子,里面躺着一只黑色手套,我把这只手套拿起来,翻看,发现里面暗藏玄机,原来里面还有一只小手套,我两只手套抽分开,里面那只小手套是我的,我记得应该是他那次车祸,我用它来给他捂伤口的,而我的另一只早已遗失。
“大手拉小手。”寓意我再明白不过了。
“请你戴上这手套,就让它代替我把你的手握牢,用两双手一起对着星星祈祷,祈祷没有我在你身边雪不要下太早。”那是我俩分手后的第一个冬天他想对说却有没说出口的独白。
我把两只手套捂在胸口,仰躺在塌塌米上,看着斜墙上贴着吴慰笔力遒劲的四个大字:“小心碰头!!!”泪水静静地滑落。
2004年的大年夜我一个人度过,到了暖春三月,吴慰与我,仍是衡阳雁断。
我在阁楼的窗户上悬了几块酱油肉,我幻想他如果看到了,又来找我吵架。
但他没来,警察却来了,原来邻居报警说我们家有人把狗杀了,还狗肉晾起来。警察叫我把肉取下来,他们要带回去化验,而且警告我在没有结果以前不要再挂任何的肉上去了。
举报我的邻居是一位独居的大爷,房东太太曾经撬了他家的门,投诉过他家的狗,他则投诉过我们家的音响和花园。两个老人斗法似的,一来一去。
Alex在二月回法国了,小楼里显得更安静了,三汉子工作室也就此解体,也再没接过生意。
早上我们发现二楼的厨房的桌子上没有摆着面包,心想大概是房东太太感冒了,通常她生病的话便不为我们做面包了。Kiki下楼去问房东太太,推开门,便是一声惨叫。房东太太躺在地上,已经不醒人事,那天救护车来的特别的慢,我们三个人蹲在她旁边,我握着她的手,已经有些冰凉了。
医生说房东太太有心机梗塞的旧疾,因为没有及时抢救,那天我们天人永诀了。
几天后我们参加了房东太太的葬礼,葬礼很冷清,我看到邻居大爷穿着一身银色的西装,站在灵柩前,低头祈祷。
第二个礼拜,我们三人收到市政厅一封信,信上说要我们一个星期内搬走,因为房东太太在过身前已经立了遗嘱,她安排了自己的葬礼,还表示死后要将房子卖掉,把所得钱款捐给荷兰心脏移植协会。
我们收到信的第二天,家里又来了几个政府工作人员,其中一位说老太太遗嘱里还有条款,受惠人是我们几个房客与隔壁大爷。
她把一楼的壁画和锅子、烤炉等送给我,把桌子和一些书等送给David,Kiki也得了一些东西,而家里咖啡机等送给了隔壁大爷。
我们陆续搬走了,我又搬到了CRB。
搬家那天小P来接我,他见我抱着锅子站在门口,便说:“村姑!CRB里基本设施都有了,你抱这一堆垃圾回去干什么?”
“你不懂,这是遗产!”我把头抬得老高,因为心里淹水了。
“里面还有只烤箱,你给安置安置。”我又对他说。
“大姐,那个庞然大物怎么搬?而且已经旧成那样了!”小P进屋看了一下,哇哇大叫。
终于我们还是放弃它。有些东西你很想带走,却无法带走,结果只得舍弃,但我们的行李轻了,心事却重了,我觉得对不起房东太太,这情感是一个活着的晚辈对一个已逝长者的愧疚,她不让我们在家讲除荷兰语以外的语言,她不让我们吃油炸的食物,她逼我们买她做的面包,那是因为她希望我们能顺利通过学校的荷兰语考试,她怕我们营养不均,她怕我们不吃早饭就去上学。
小P推着车,我抱着锅子跟在他后面,我们往CRB走,我忍不住回头再看看这栋老房子,那些爱为什么直到回头才看到?
“我们要留学不留爱吗?”我轻轻地说,我心里却有个很清晰地答案:我做不到!我留住了房东太太的爱,吴慰的爱,甚至是Steven的爱,那些爱都是深刻且珍贵的,却让我感到无比的沉重,重到无法的牵起嘴角做出一个虚伪的微笑。
小P回过头来,什么都没说,只是把我锅子接了过去放入车后的袋子里。
也许吴慰随时会回来,我怕他会找不到我,所以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回到这里来转转,房东太太的房子的门上已经贴了字条,正在欲售,而我在下面不起眼的地方用中文写上:“慰,我在CRB39号。”
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,邻居大爷的花园里已经搬出了桌椅,他又开始了享受暖风,享受阳光,享受午后的咖啡时间。
但他隔壁的园子已经空了,开始长出野草,大爷时不时的回过头看看,发现他的邻居,他的敌人已经不在了。
无敌是最寂寞的。他家的老狗蹲在他脚边,那是他剩下的唯一的朋友。
我终于明白了房东太太那天为什么要撬开他家门,因为如果他在家突然死去,没人会发现,也许只到尸体发出气味,才会招来外人。想起他们以前远远地对看,其实那是一种守护。
我回到家打开电脑,收到两封电邮。
一封是王静写来的,里面有她家儿子的照片,她说我干儿子已经长牙了,而她还说她和“维他命”的爱情也开始长出了新芽,她感悟出结婚就像得了斯德格摩综合症,相处久了,不幸渐成幸福,只要男人爱女人,女人可以强迫自己幸福。
另一封来自澳大利亚的Jennifer,她已经申请下一个移民指数很高的专业,还说交了一个蓝眼睛的男朋友。她和我及吴慰三人之间的一切恩怨都被彼此淡忘了,因为爱情而失去的友情,也将因为得到新的爱情而重新获得友情。我们都学会了向前看。
我打开QQ,发现小方在线,他出事后便回国了。
我说:“你好吗?”
久久才得到他一句话:“好,男不男,女不女的。”这应该算是好吧,因为他终于可以拿自己开玩笑了。
我不能接着他的话玩笑下去,那样有挖苦的嫌疑,只得说:“小P最近又失恋了。”
他说:“失恋算什么!他有他弟弟在,什么时候时候都能再战情场,而我……想当年,顶风尿十丈,叹如今,顺风尿湿鞋。”
我说:“你会讲笑就好了,我放心。”
我给我王静和Jennifer回了一封简短的电邮,说我已经搬家了。人前我继续微笑,不诉离伤。
第二天我再去房东太太的旧居,发现我贴在上面的字条已经不见了,我发足狂奔,朝CRB。
远远地我看到一个背影。
<71> 爱死寂寞人 [完结篇]
那个背影转过身来,那一瞬间我感到窒息。
他朝我快步走来,而我却依然停在原地,任他将我搂在怀里,“我好想你!”他说。
“你好吗?”我抬头看着他,感觉对他已经有了微小的陌生感,他是Steven,从美国回来的Steven。
他手里拿着我写在房东太太门上的字条,这字条我每隔几天都会去更新的,我伸手欲拿回字条,他却把它随手扔在了地上。
“别等了,他,他也许已经死了。”Steven说。
“不,不会的!”我拼命地摇头。
“我爸爸叫辉哥查过,那辆撞毁了的车子已经找到了。”Steven小心翼翼地说。
我感觉天空突然变得漆黑如墨,一下向我脑门压了下来。
对于绝望的消息我不愿去追问,也许是不敢。
Steven叫我毕业后和他一起去美国,我没答应他,于是他落寞的地走了,而我仍然留在了原地,却感觉希望就像积雪在慢慢的融化。
某一天Tina的男朋友告诉她自己在巴黎的街头看到吴慰,或者是一个很像吴慰的男子。
又一夜我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却一直没说话,顿了一分钟,挂断。
我收集吴慰活着的线索,自我安慰,我把思念铸成了一把刑具,自我恐吓。我站在希望和绝望之间,自我挣扎。
只是我一直都学不会离别,学不会逃脱。
十月,我去参加徐建华的女儿满月酒,我本是穿着一件束腰的黑色大衣,小P笑说这件衣服喜丧两相宜,于是我换了一件大红色的外套,小P又说穿大红色喜庆的有些突兀,于是我照旧还是穿了黑大衣去。
徐建华安排了一个他屯大的学弟袁俊和我同席,还一个劲的替我们敲边锣鼓:“袁俊,给玛丽夹菜,夹菜。”
袁俊是个大近视,夹了一块暗红的老姜放在我的盘里,深情款款地说:“你吃块肉。”
我看了徐建华一眼,勉强把老姜咽了下去,我也夹了一块老姜给他,“你也吃一块肉。”他放入了嘴里。
“我们来划拳!”我伸出手,对袁俊说。
“什么?”他楞了一下,说:“我不会!”
“那我们喝酒,我先干为敬。”我端起杯子,把满满的一杯啤酒一口灌了下去。
袁俊战战兢兢地替我捧场:“好酒量,好酒量!”
我打了个酒嗝,道:“你也来。”
“我,我上个洗手间。”他起身离开位子,我以为他怕了。
不想他上了趟厕所回来变得豪情万丈,端起杯子学我一口干了,放下杯子,道:“我们再喝。”
我没给他倒酒,拿出纸笔,写了三个英文单字,递给他,“袁先生,你读读看!”
“peace war found!”他读了起来。
“再大点声。”
“peace war found!”他高了一度音,邻桌的一位和他相熟的老兄朝他嚷:“俊,你醉了?放个屁也嚷嚷!”
袁俊窘了,把纸揉在手心,无辜地看着我,他没再和我喝酒,匆匆地走了。
徐建华怪我把他精心安排的相亲酒给搅黄了,我告诉他我一直没学会在人前佯装淑德,他却说这是恋爱留下的后遗症,我没再回话,也许他的话是对的。吴慰的名字,是我心上永恒的门牌,我可以为任何一个男人开门,但他们却都会望而却步的。
2005年的圣诞节,我仍然去中餐馆打工,我结束一天的工作,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商铺门口扎着五颜六色的彩灯,绿色的圣诞树、红色圣诞老人随处可见,街上飘荡着一种寒冷和热闹结合的暧昧气味,让快乐的人更快乐,让孤独的人更孤独。
一个不留神,我重重地跌在了地上,我爬起来,看着路边一家商的橱窗,映出一个自己:一个穿着长式羽绒服的女孩,带着一个有毛边的帽子。我想起2001年的那个冬天的早上,吴慰说我臃肿如爱斯基摩人。
“爱斯基摩人?爱死寂寞的人。”我对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。孤独的人不一定寂寞,多情的人却有最深的寂寞。
我继续往前走,天空开始飘雪,我伸出手接着纷然落下的雪花,看它们在我的手心慢慢的融化,成了一滴滴晶莹的泪水。
也许我和吴慰就是两朵孤独的雪花,在爱情的天地里纵情地飘洒,却被寒风吹散,被时间融化。而他现在留给我的便只有泪水。
两点的时候雪停了,我走到窗前,对着玻璃呵气成雾,写下:“吴慰,我等你!”
我对自己说没有他的拥抱我也不允许自己感冒。
-END-
这层楼我先占着,一有新的我马上来更新啊~ |
|
相信爱情,佩服别人的坚定相守。
缺乏安全感,一直犹豫。讨厌对着说不通的陌生人。过于敏感,自我保护。
一个人写字,企图找到爱情的出口,幸福的结局。却找到疼痛的答案。
终于明白,爱是一个人的冷暖自知,无关其他。 |
|